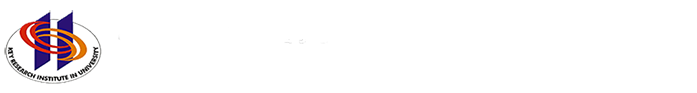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论坛·“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33讲
2025年11月27日上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33讲“自然”,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山西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王中江教授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陈少明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之前,陈少明教授谈到,在中国哲学史上,“自然”与“气”的概念有些相似,是一个比较抽象、难以精确定义的词。“自然”的内涵非常丰富,它不仅限于我们今天理解的哲学范畴,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艺术、宗教、政治到为人处世,这个概念被广泛运用。因此,它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和代表性的概念。若能够深入理解并阐明“自然”的深层含义,必将增进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其影响力会远超一般词汇。王中江教授在这一领域深耕多年,卓有建树,期待他的分享。
一、Nature的东渐:从“本性”到“自然”
王中江教授认为,“自然”符号是一个影响世界的巨链之一。在东西方大传统中,先是各自独自发展,几千年后融合,产生了新的形态。两大传统中的“自然”符号,历时中源远流长,共时中丰富多彩。从生长到自在,从本性到实体,从根源到合理,从必然到应然,从莫为到境界,义蕴形态,不一而足。类似中可见差异,殊别中可观类似性。一探究竟,意味深长。
清末以降,中国人使用的“自然”概念,同中国历史上古典的用法相比,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同西语nature的东渐息息相关。这个词最早在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中文最初译自拉丁文。形容词,当时译或译为“天然的”,或译为“性”;如《寰有诠》《性学觕述》等译为“性”,指自然哲学natural philosophy,包括物理学及灵魂论。用“性”比较多,比如 “性理之道”,指的也是natural philosophy;在《寰有诠》中,傅汎际解释天体、形天的自动运行,也使用了“自然”一词,说它们是“因性自然之动”。不管是作为名词,还是作为形容词,大都译为“性”(或“本性”、“性理”);偶有译为“自然”“自然的”。到了晚清,主要由传教士编纂的英华辞典,大都没有将nature译为“自然”,而主要是译为“性”“性质”“天地”和“宇宙”等。
这个词移植到日本也比较早。日本从幕府末期到明治维新,一些辞典大都没有把nature译为“自然”,而是译为“性”“性质”等。随着用“自然”去理解和翻译nature,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从1891年大槻文彦的《言海》和1894年物集高见的《日本大辞林》开始,这个词都明确被翻译为“自然”,并很快普遍化。日本的这一变化很快就影响到了中国。如蔡元培翻译出版的《哲学要领》中称自然“即物质世界之义”。自1900年后,大量的哲学著作、教科书和工具书,都迅速接受了这种意义上的“自然”译名和用法,格致学、格物学名称等不久也被“自然科学”之名代替了。
二、欧洲物理的“自然”及中国“自然”的“物理实体化”
王中江教授指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自然”这个词主要有两个用法:一是指作为科学和技术物件的自然界和万物;二是作为一种良好状态的非造作意义上的“自然而然”。但第一种意义是欧洲“Nature”概念带到中国古典“自然”概念中的;第二种用法是中国固有的。这是中国古典“自然”的“实体化”过程,也是欧洲“自然”的本土化历程。
从20世纪初开始,这种中文“自然”具有首要意义,就是物理自然和自然界。如严复开始让步并接受日译“自然”的译名和用法,以“自然”为万物的存在和实体。 这一变化不仅是东方对欧洲“自然”概念认识和理解的变化,而且也是对中国古典“自然”概念的一大转变。在这种转变之前,中国古典中的“自然”概念同欧洲“自然”概念的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欧洲的“自然”具有指称自然界和大千世界或万物实体和物理客体的意义,而在中国古典中,这种实体意义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确实非常稀薄。
欧洲实体意义上自然在中国古典中十分罕见,缘于两点。一是中国古典中将“自然”用作万物的根本(如道、气和佛)的本性、用作万物的存在方式这两种意义非常强大。二是用来指称自然界、大千世界的词汇并不缺乏,如物、万物、天、天地、宇宙等具有这方面的用法,有了这些词汇就没有再为“自然”赋予这方面的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语nature等移植到东西时,主要是从性、本性和性质上去翻译和解释,而没有用“自然”。
而中国非物质实体的“自然”概念之所以能够摄入物质实体的意义,一者由于欧洲自然概念的东渐,一开始就有将natural理解和翻译为“自然的”,由于事物和宇宙根本的本性,由于事物和宇宙根本的存在方式,在中国古典中说又都是同事物、宇宙的根本是一体的;二者由于事物的本性主要指事物的根据和本质,不指事物的现象和形体,而大千世界,既包括了前者,也包括了后者,将“自然”的“本性”义一扩大就可以两者兼有,但契机则是东西“自然”概念的相遇和融合。
由于这种融合,中国古典的自然概念在近代就被赋予了客体、现象世界等实体意义,与此相关的一些词汇,如自然力、自然法、自然规律、自然人、自然界、自然物、自然地理等词汇产生了,整体研究自然和运用自然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技术文明也产生了。这是“自然”概念的一个革命性变化,也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革命性变化。
三、世界内在原因和自发性的自然:自然对超自然
关于近代西方在科学影响下的哲学上的“自然”概念,王中江教授梳理出这样几种含义:其一,自然是整个实在和现实的总和,宇宙都是由自然物构成的;其二,世界和宇宙都是“自然”的结果,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没有“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也无须假定其他终极的实体或根据;其三,“自然”现象具有规则和齐一性,它是可以被认知的,科学的经验方法是认识自然的最有效方式。其四,人类是自然活动的结果和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精神和意识是大脑的活动和过程的产物,没有独立的精神实体。
这种物质实体自然的中国化,同时带来的还有“机械自然观”和“因果自然”的中国的兴起。严复和胡适则是其中的代表。胡适从宇宙和世界原本是自己造就自己的“自然”来解释和看待宇宙,认为宇宙及其万物纯粹是宇宙自身活动的“自然”结果;反的方面是胡适拒绝一切超自然的力量,否认宇宙和万物是由最高的“绝对因”特别是“超自然”的力量——“神”主宰的。
对天地万物的存在及其根据,借用《庄子·则阳》篇的说法,一是“莫为”,一是与此相反的“或使”。“或使说”认为天地万物的存在和变化取决于主使者的作用;与此相反,“莫为说”则认为宇宙和万物何以如此则是它们自身的原因所致,在它们自身之外没有什么力量决定它们。从“莫为”来看道家的“自然”,它既具有“非人为”的意义,类似于荀子批评庄子说的“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天”;又具有“非主使”的意义,这是将天地、万物的存在和变化的原因都归结为它们自身,否认或使者或主宰者。一般所称的道家的“自然主义”,可以叫做宽泛意义上的“莫为说”。道家“自然”的这两种意义都是在老子之后演变出来的。对胡适来说,道家自然主义“非主宰”的方面值得赞扬,而“非人为”的方面则需要克服。
四、“自然”与事物内在的本性
重新回看中国“自然”概念的翻译史,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为何清末的传教士,中国和日本的哲学家们,都把nature理解为“性”?在欧洲的历史里面这个词是不是有很强烈的本性的意思?中国的自然概念是否有本性的意思?如若有,为何早期没有用自然去翻译nature?
王中江教授解释说,原因之一是传教士或者中国早期的思想家没有看到中国自然概念里面本性概念的重要性或者复杂性,然而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的时候,用“自然”去翻译nature的时候,便表明这两个词之间在事物的性质上,在事物的本性上,确实具有可比性,或者有类似性的部分。
中国的自然概念,为“自然”赋予性的意思,是在《庄子》里面开始出现的。自然的性,就是事物的天性或者人的天德。人有天德、天真,事物也有它自己本来的本性。在道家中,“物性”主要是由事物的“德”表现,叫做“物德论”。在儒家中,人的本性叫做“性”,“物的性”又叫做“理”。在佛教里面说的“自然”又被用来指称事物的现象,“自然”是“空”,“自然”又成了“无自性”的意思。章太炎发展了佛教的“自然”现象存在的意义,现象的自然的本性是空。
《庄子》之后,“自然”的本性概念经过演变,从汉代以后开始经历哲学“本体化”。如《老子想尔注》中所言,“自然”与“道”“同号异体”,相互为法。隋唐时期佛道论辩,有“道”与“自然”之争。宋明理学中有“天理自然”与“自然天理”的说法。不同于必然、当然等,理之“自然”和“自然”之“理”的自然:一指“自身”如此;二指“本然”如此;三是指“固然”如此。
五、“自然”与“人为”
王中江教授认为,天与人、自然与人或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分与合充满着复杂的情调。现在用作“非人工”的“自然”,是把人类的活动及其结果同纯粹物理世界和物质世界自身的活动及其结果区分开。这种“自然”是相对于“人”的狭义的“自然”。
在赞美自然与抵制违背自然和反对人为的背反中,合乎自然被赞美,背离自然被谴责古今东西。例如庄子美化“天”,热衷于“天人合一”,菲薄人工,更批评背反“天”的“人为”和“造作”。庄子用“天”和“自然”表达的“自然主义”,主要强调非人工、非人为、非造作的意义。 在《庄子》中,“天”或“天德”体现在人身上是人的天性和本性。“天”是纯真的美德和价值,来源于天的人的天性也是纯真(就此来说,庄子的人性论也可以说是性真论),人保持和表现他的天性,他就达到了天人合一,这是庄子的信念。但在现实中,人们不免损害甚至失去他们的天性美。庄子强调天、天真、纯朴等价值,就是为了让人们保持这些东西。他之所以批评人工、人为、造作,批评人的故意、有意识,在他看来这些东西破坏了人的天性真。
六、回到源头和早期:老子和黄老学的“自然”
在王中江教授看来,作为万物实体的“自然”是就一切事物及其现象的整体而言,作为事物本性的“自然”强调的是事物固有的内在特性和依据。与这两种含义密切关联的是,“自然”还具有事物“自成”与“自己造就”的意涵。从逻辑上说,作为万物实体和本性的“自然”,则是自己造就的“自然”的前提。但从道家自然概念的产生及演变过程来说,“自己造就”和“自成”的“自然”却是先行产生的,万物实体和本性的自然则是在此之后演变出来的。此外,事物自成和自己造就的自然,同上述非主使的莫为自然(“自生”“自化”)有某种类似性。但在后者,万物的自生、自化同否定主使者、主宰者、神意论和目的论是一体的两面;在前者中,万物自成的“自然”,则是同道和圣人的“无为”联系在一起。
这是老子创立的“自然”,也是中国“自然”的最初意义,其他的意义都是在此之后演变出来的。老子用的自然,是指事物或人的“自我造就”,或事物自己造就了自己,用两个字表示这个意思,就是“自成”。逻辑上同“万物”的本性、实体和“人”的本性联系在一起,指万物和人的“活动方式”“存在方式”,指事物的自组织性和人的自发性。从现实来说,事物自己造就自己的自然,同时又是万物实体及其本性的自然的实现。
老子所谓“自然”,没有本性的意思,指称事物本性的词汇是“德”(物德、物性),到了黄老学,“德”有物德的意义,人的德就变成了人的本性——“人情”。这样黄老学的“自然”就变成了事物由内在之德驱动的自我变化、成长和自组织性,变成了人由内在自己的性情而驱动人的自主性和自发性活动及其结果即自我塑造和自我。
七、讲座回响
讲座结束,陈少明教授作出评议,他认为王中江教授的讲座给予了两点重要启发。
第一,关于“自然”这一概念的演变脉络,以往讨论多聚焦于本土语境,而本次讲座揭示出“自然”作为一个现代常用概念,其涵义的生成经历了从西方到日本、再到中国的跨文化流转过程。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然”,未必完全源自中国传统固有的意涵,也未必是传统中隐而未发的观念,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外来文化影响与重构的产物。“自然”作为术语与我们日常用语中的词汇有所不同:它既是学术研究中的专业概念,又广泛渗透于日常生活,因此在文化与实践层面具有标志性意义。
第二,这一概念具有鲜明的系统性与流动性。它在思想研究中呈现出一种“网状关联”而非“金字塔层级”的结构特征。具体而言,同一个词在不同学派或学者笔下可能衍生出不同涵义,说明思想的重心并不固着于词语本身,而在于其引发的思辨维度。同时,“自然”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传递或静态隶属,它并非由某位思想家在单一体系中建构而成,而是贯穿于整个历史演变过程。通过追踪这样一个概念的轨迹,我们得以窥见更广阔的思想图景。它不像一座概念的金字塔,而更似一条河流,不断地流动、交织;也如同一张网络,其中每个概念并无绝对的高下之分,而是根据具体语境与联结对象生成新的意义。因此,在理解思想史或哲学史时,我们必须对这些流动的、网络化的概念关系具备深刻的洞察,才能更全面地把握思想的真实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