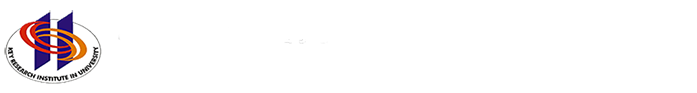“启蒙精神与马克思”青年工作坊
2022年11月26日,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马哲所”)、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和广东省马克思主义学会联合主办的“启蒙精神与马克思”青年工作坊在线上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深圳大学和中山大学等高校和《学术研究》、《哲学分析》编辑部的近三十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本次工作坊共设两场主题报告和五个讨论专场,吸引了全国各地共150多名师生参加。
开幕式由会议召集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张米兰助理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马哲所所长张伟教授致欢迎辞。张伟主任对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衷心感谢学界朋友对本次青年工作坊的大力支持。他指出,“启蒙精神与马克思”这一议题同时处于学科交叉和学术前沿,具有很强的学理性和前瞻性;本次参会的学者以中青年为主,横贯多个研究领域和不同学术背景,相信定能碰撞出精彩的思想火花。
清华大学夏莹教授和中山大学马天俊教授分别做主题报告。夏莹教授在以《启蒙与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形成》为题的报告中指出,基于彰显着带有未来指向和现实社会运动意涵的理论立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可视为对法国启蒙运动中社会的唯物主义传统的一种扬弃;由此,这种新唯物主义之本质规定也就包含着启蒙思想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继承关系,与启蒙之本质处于同一理论论域之中。由《博士论文》这一文本对伊壁鸠鲁的判定可看出,马克思对启蒙精神的理解在于理性自其诞生以来对于绝对的、超验的、神性的、强加于事物之上的任何原则的拒斥,即对破除神性的理性原则的推崇和保持;对此的弘扬恰需要诉诸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定向以赋予其独特的实践原则。
马天俊教授以《启蒙:马克思的象征意义》为题,从几个方面提示了启蒙与马克思的可能的关联:首先,作为马克思出生和成长地的莱茵省由于地缘状况而同时兼具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法兰西性质”和既反法国又要从法国学习现代化的矛盾的普鲁士性质;其次,以西欧(英、法、德)为中心的启蒙潮流固然复杂,但启蒙最初的朴素含义就是言论自由权利;再次,青年马克思的命运处于同时代德语地区共同的体制背景即对启蒙的反动,为此他从欧洲大陆辗转到英国,这一地域的流动有其深刻的时代方向性。
上午进行的本次会议第一场题为“科学与经济理论中的启蒙问题”,由中山大学黄学胜副教授主持。吉林大学田冠浩教授在题为《伊壁鸠鲁的两幅现代面孔:启蒙与马克思》的报告中指出,伊壁鸠鲁思想深入参与了现代启蒙和现代社会的塑造,伊壁鸠鲁对目的论的批判不仅启发了启蒙时代的科学,还从根本上影响了启蒙政治哲学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基调;通过对伊壁鸠鲁的重新阐释,马克思得以告别启蒙的抽象自由,转向真正的“现实的个人”,在“历史科学”和社会主义的筹划中重塑启蒙。南京大学李乾坤副教授在题为《马克思对启蒙货币理论的批判》的报告中指出,启蒙货币理论分享了共同的思想范式——“自然性”和价值符号说,后者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包含了其内在矛盾,引发了数次争论;青年马克思对货币的哲学判断和《伦敦笔记》及其后马克思对货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构成了马克思对启蒙货币理论的两个阶段的批判;后者确立了将货币根植于资本之中的问题式,是其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切入点。深圳大学张守奎教授在《青年马克思与启蒙传统的内在关联与限度》的报告中指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乃是启蒙在政治领域的实践效果;黑格尔对近代民主政治的历史的、辩证的批判和他对民主的理念与民主理念的具体化样式的区分,以及马克思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对民主的内容与民主的形式之差别的阐述,启示我们既要继承启蒙传统的精神遗产,又要超越启蒙传统只是满足于形式民主的局限,深化民主的实体性内容并使之具体化。评议与讨论环节中,李乾坤副教授高度评价田冠浩教授选题的创新性及对马哲研究的重要意义,就用原子特质理解社会与唯物史观之基本定向之间可能存在的背反以及如何区别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和不自觉地继承的黑格尔的观点提出了疑问。张守奎教授肯定了李乾坤副教授从微观意义上对以往研究的推进,对启蒙货币理论的启蒙性质提出疑问。华东师范大学陆凯华副教授建议纳入马克思后期文本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中对启蒙的精神层次和实际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张力的论述,以补足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的思考。
本次会议第二场题为“反思启蒙:理性、道德与合理化”,由《哲学分析》编辑部牛婷婷老师主持。中山大学黄学胜副教授在题为《“启蒙的再启蒙”:马克思对“思想的统治”的批判及其意义》的报告中聚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思想的统治”的批判及其与启蒙问题的关联:青年黑格尔派实质向往的是法国启蒙的原则和路径,但却止步于理性的形而上学传统和思想观念斗争,与其母体即黑格尔哲学、各式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陷于“思想的统治”;马克思在对其的批判中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变革了近代西方启蒙人道理想之实现的逻辑,实现了从激进启蒙到反思启蒙再到稳健启蒙以及从资产阶级启蒙到无产阶级启蒙的转向,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康子兴副教授在《商业社会与现代君主国》中介绍了伊什特万·洪特(Istvan Hont)在其遗著中开启的“商业社会的政治视野”及对现代政治的思索:孟德斯鸠的特洛格洛迪特人传说既是对道德真理的抒发,也是关于历史的寓言;以及孟德斯鸠对不平等及现代君主国的论述也为卢梭与斯密的思考塑造了语境。华东师范大学陆凯华副教授在《启蒙理性视域中的主-奴辩证法及其三重》中讨论了阿多诺通过将辩证法中的实践要素重新纳入思辨过程而演绎出的主奴辩证法在启蒙理性视野下的三重变型——概念与直观、知识与信仰、以及分工与统治的辩证法,并指认了阿多诺由此接续马克思、韦伯与卢卡奇的思想资源。评议与讨论环节中,田冠浩教授指出,思想的统治既是启蒙的重要成就,又重新建立起知识的等级秩序而遮蔽了实践领域的变化和现实的人;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实现了对英法启蒙的深刻的概念把握,马克思通过更彻底地理解人及其社会生活完成了更彻底的宗教批判。中山大学黄涛副教授就《波斯人信札》具体的文本理解及论证合法性等问题与康子兴副教授进行了交流。张守奎教授就“非图像的图像的概念辩证法”何以超越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辩证法而通达经验质料性、以具有隐喻色彩的前概念的模仿机制理解传统形而上学的可操作性两个方面提出了疑问。
下午进行的本次会议第三场题为“反思启蒙:从政治神学到权力批判”,由中山大学覃万历副研究员主持。中山大学林钊教授在《施蒂纳与例外状态》的报告中认为,施蒂纳通过对费尔巴哈本质主义的批判,比施米特更早指出了自由主义解放面具下的神学本质;前者以“利己主义者联盟”瓦解了国家,暗藏着破解以例外状态为根本问题的现代政治的可能。南开大学夏钊助理研究员在《启蒙与批判》的报告中指出,得益于黑格尔对启蒙的分析,马克思将有用性视野中的国民经济学资源吸收进来,发展出具有三重功能——改造世界和社会化生产的社会理论功能、构造自身认知行为关系的认识论功能、培养教化解放意识的规范-实践功能——的劳动理论以实现启蒙与批判的综合,现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恰恰也是以此为方向进而实行的对劳动方式的转化方案。上海大学关山彤讲师在《从先验批判到财产共和国----哈特与奈格里如何谈论启蒙》的报告中,由福柯对启蒙问题的转化出发,讨论了奈格里和哈特何以在对财产共和国的批判中以“非主流的”方式切近了康德的启蒙精神和先验批判方法,前者以更为激进的、靠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建构路径改造了启蒙的原则。评议与讨论环节中,广东财经大学邓先珍副教授指出“主权权力行使何以可能”的问题更能概括林钊教授报告的核心,并就何以在启蒙政治的视野下打通施米特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等议题与林钊教授进行了讨论。中山大学柳成雅助理教授认为,启蒙与批判是具有异质性的两个概念,用启蒙与批判的关系作为概括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主线,对于把握其整体性和独特性而言,是存在局限的。夏钊助理研究员就奈格里和哈特是否退回到启蒙以及何以在对生命内在力量的支持的观点上超越康德提出了疑问,指出前者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建立内在联系尚需更有力的论证。
本次会议第四场题为“启蒙的后果:社会性、情感主义与民族性”,由《学术研究》编辑部罗苹老师主持。同济大学梁冰洋助理教授在《马克思对施蒂纳社会观的批判》报告中指出,施蒂纳基于对十九世纪涌现的政治集体主义与中央集权问题的关注,在对社会组织与个体自治关系的思考中,带有明显的反社会性质;但其所关注的个体并非“现实的个人”,但所谓非正式组织本身也意味着一种统一原则(利己主义)的确立,联盟同样成为“虚幻的共同体”。中山大学卢俊豪博士后在《人性善恶的情感脉络:英国情感主义伦理学的兴起与道德善的科学化》中认为,基于人类官能的情感主义伦理学起于从“性恶”到“性善”到人性论视角转换,发轫于“科学心灵哲学”和“实践伦理主张”两大基石,完成于以“同情机制”为核心的道德剖析,并把道德从“彼岸世界的救赎”拉回到“此岸世界的公共生活”中,为道德善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化理解,由此展现了道德情感主义关于人性善恶的启蒙逻辑。华中科技大学张炯博士后在《论休谟思想中的民族性问题》报告中指出,和孟德斯鸠等认为气候等环境因素影响民族性的形成不同,休谟认为道德因素才是塑造民族性的关键;其中闪烁的启蒙时代白人思想家普遍的种族偏见和启蒙对自由与人性的追求并不冲突,却启示我们警惕西方启蒙在民族性问题上的固有缺陷即对民族性的种族化理解。评议与讨论环节中,林钊教授指出,施蒂纳处理的不是我与他人、集体、社会的伦理问题,而是自我的伦理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受马克思影响而对其现实操作性展开的批判可能都是一种错位的批判;施蒂纳不关心占有物,只关心自我如何不被自己的观念占有,这既是其与马克思之间的错位,也是与庸俗利己主义即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之间的错位。张米兰助理教授对以性恶论概念表述基督教传统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强调“感觉”和“社会性”在理解苏格兰启蒙思想方面的重要性。梁冰洋助理教授认为,休谟思想的民族性体现为处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两种启蒙之间而呈现的经验主义至上的情感主义,可能陷入以日耳曼民族解构凯尔特民族的悖论,这就为道德的合法性以及休谟道德学说与法权学说的统一埋下了隐患。
本次会议第五场题为“启蒙的地方性:苏格兰的制度与经验”,由中山大学林钊教授主持。中山大学赵雨淘助理教授在《商业社会与人民主权的结合:从西耶斯反思斯密和卢梭》报告中认为,西耶斯的国民制宪权理论实现了对斯密式商业社会与卢梭式人民主权的综合,一方面通过国民制宪清除特权阶级,将商业社会转化为具有正当身份和行动能力的政治统一体,另一方面反对不受限制的直接民主制,通过商业社会的分工原则限制公共权力、重塑人民主权;如此的结合或平衡固然不易达到,但只有向这一方向前进,我们才可能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时代,重建一种更理想也更现实的政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博士候选人张帅在《制度建设与价值理想:休谟对光荣革命》中指出,理解光荣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休谟史学工作的中心,比起从碎片化的段落中揣度他的党派倾向,更重要的是抓住支配其历史写作的哲学精神;光荣革命在建立足以应对国际竞争的财政-军事国家的同时通过有限君主制的根本原则确立了崭新的自由秩序;澄清英格兰政体何以兼具力量和自由,是理解休谟史学工作的枢纽。中山大学张米兰助理教授在《论马克思与斯密对自然概念的使用》报告中对比了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对自然概念的使用:前者主张自然从内部给事物的运动提供原因,事物通过习惯的培养与自然秩序达成内部的统一,具有同时代少见的古典主义色彩;后者将其理解为以人为主体的自发与自为的结合而非单纯给定的质料;二者都涉及到对偏离自然的解释,但前者将其视为自然的引力的表现,后者则视其为革命或转型的契机。评议与讨论环节中,卢俊豪博士后从两个角度提出疑问:一是商业社会与人民主权的张力究竟是两个概念自身的张力还是西耶斯双重面孔的张力,二是西耶斯给出的这一张力的解决之道能否破解对西耶斯的极权主义民主解读和恶性循环问题。赵雨淘助理教授就休谟在历史叙事中的看法与他更系统的政治哲学之间的衔接以及如何在复杂的历史叙事中学到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即克服英国例外论的问题与张帅进行了讨论。覃万历副研究员补充了亚里士多德对自然运动的双重介定——自身本性产生的运动与外力的运动,就展开斯密与马克思自然概念的内在张力、分享的启蒙背景以及区分直接使用和隐喻使用等给出了建议。
闭幕式由张米兰助理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哲所户晓坤教授做会议总结。户晓坤教授指出,在启蒙精神与马克思所构筑的问题视域中存在着高度紧张的关系,启蒙作为对特定民族精神与社会生活过程的理论表达,关联着马克思时代的革命性变革,形成了与之不断对话的可能性,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开启了对启蒙及其精神传统的总体性反思,今天我们仍然以更高的哲学原则和更切身的问题意识承载这一时代任务负重前行。她代表中山大学马哲所再次对与会学者表达感谢。张米兰助理教授期待“启蒙精神与马克思”青年工作坊不断凝聚共识,形成规模,开展为系列性的学术活动。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的线下相会!